撰文/约翰∙斯皮克曼
翻译/张丽娜
我的一位周姓朋友的妻子特别害怕蜘蛛。每次看见蜘蛛,她都几近歇斯底里的边缘,直到周先生捉到蜘蛛并将它驱逐出公寓。这位女士也不喜欢蟑螂,但那仅仅是厌恶,只有蜘蛛能激起她内心深处真正的恐惧。然而细究起来,这种恐惧的产生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北京现有的蜘蛛都没有毒性,在她的故乡也没有发现过有毒的蜘蛛,她在童年时代也没有经历任何与蜘蛛相关的创伤。她自己这样描述道:“我想这种恐惧来自我的DNA,可能我的祖母经历过与蜘蛛有关的恐怖事情,然后她将这个遗传给了我。”
这解释很有意思,不过,恐怕绝大多数生物学家会对这个所谓“祖母遗传”的解释不屑一顾,因为这与分子生物学中的中心法则(genetic central dogma)背道而驰。中心法则,是指由DNA编码的遗传信息转录传递给RNA,再从RNA传递给蛋白质,即完成遗传信息的转录和翻译的过程。这一信息流是严格的单向传递。DNA的序列可能发生改变(突变),但这是随机的。因此,周太太对蜘蛛的恐惧遗传自害怕蜘蛛的祖母,这一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根据中心法则,周太太的祖母不可能在经历与蜘蛛有关的创伤性事件后对自己的DNA编码进行相应的修改,从而将这一恐惧遗传给后代。迄今为止,人们尚未发现任何机制能实现非随机性的DNA编码突变。
早在18世纪有人提出一个观点——后天获得性状遗传,即人们可能会遗传祖先们在生活过程中受环境影响而后天获得的性状。此观点得到法国著名博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的推崇,因此也被称为“拉马克主义”。这一观点在19世纪极为流行,甚至达尔文也赞同该观点。然而,随着人们对遗传机制的逐渐认识,发现遗传信息是按照DNA-RNA-蛋白质进行传递,很显然后天获得的性状是不可能遗传的。也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类遗传不会发生。比如,如果某个人在车祸中不幸失去一条腿,他之后生的孩子不会生来就少一条腿。后天获得的性状(一条腿缺失)不会反向将信息传递到DNA继而影响该个体的后代。著名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曾经指出:5000多年来某些宗教中一直存在对未成年男性施行割礼的传统,即在男子性成熟之前割去包皮。尽管割礼广泛而系统地持续了几百代,到现在这些宗教的教徒们出生时仍有包皮,从没有人遗传其男性祖先们若干代以来的获得性性状。
可能有人会提出反驳,上述获得性性状没有得到遗传是因为其不具有选择优势。拉马克主义认为获得性是特指有益的性状。如果一个人在车祸中失去一条腿,他的后代出生时也少一条腿没有任何益处。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们做了许多实验来验证大鼠是不是能获得具有选择优势的性状。其中最著名的一系列实验来自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威廉姆∙麦克杜格尔(William McDougall)。他将大鼠放入具有两条逃跑通道的水池中,其中一条通道有光照,另一条则没有。如果大鼠选择有光亮的逃跑通道,它会遭受一次电击。他的测定指标是大鼠学会使用黑暗逃跑通道前的试错次数。快速学会这一任务对大鼠来讲显然是一个优势。麦克杜格尔训练了一批大鼠,然后让其交配繁育后代,再训练它们的后代并让其继续繁育,这一过程持续了32代,用了整整15年的时间。他发现,接受训练的大鼠的后代学习该项任务的速度比亲代更快,并且随着代数的增加,学习速度越来越快。初始8代(1~8代)大鼠平均需要56次试错才能学会该任务,而最后8代(25~32代)仅需要20次就能学会。此后,阿加(Agar)及其同事们开展了一个类似的持续20年的实验,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但是,两个独立的实验中存在一个共同的令人困惑的结果:未接受训练的对照组大鼠的学习能力也逐代增强!对这一令人吃惊的结果还没有很好的解释。倒是有人将其作为轮回转世论的证据——接受训练和未接受训练大鼠的后代平等地得到了死去的接受训练大鼠的灵魂。不管怎样解释这一结果,有一点很明确,人为的训练并没有引起明显差别。因此,拉马克主义和获得性有利性状的遗传也不成立,这些结果倒是支持了后来出现的中心法则。
基于上述背景,最近在《自然 神经科学》( Nature Neuroscience) 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一些让人震惊的发现。两位来自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科学家,凯丽·雷斯勒(Kerry Ressler)和布里安·迪亚斯(Brian Dias)研究苯乙酮对小鼠的影响。这种化学物质具有一种特别的气味,有点像樱桃的味道。他们将雄性小鼠暴露于苯乙酮的气味下,同时对小鼠施以少量但疼痛的电击。小鼠很快就将气味和疼痛联系起来。最后,仅仅是苯乙酮的气味就足以使其颤栗。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早在19世纪90年代巴甫洛夫发现狗听到铃声会分泌唾液后,人们就认识到动物具有将类似事件联系起来的能力。然而,令人吃惊的是,雷斯勒和迪亚斯的实验中受训练小鼠的后代也出现了同样的恐惧特征。当苯乙酮的气味飘到它们的笼子里时,它们居然因恐惧而颤栗。联想到之前麦克杜格尔和阿加的实验,我们当然想知道:“对照组是什么情况?”答案是:没什么反应。实验中设了两个对照组,一个是未用化合物处理的对照组,对苯乙酮无反应;另一个是用一种其他气味化合物处理的对照组。有意思的是,将另一种气味和电击联系起来的小鼠,对苯乙酮也无任何反应,表明该反应是高度特异性的。这有点类似害怕蜘蛛却不怕蟑螂的情形。更加令人惊讶的是,第3代小鼠仍遗传有上述恐惧反应。除此之外,用具有恐惧反应的雄性小鼠的精子,通过人工受精得到的后代,也表现出同样的恐惧反应。人工授精排除了这样一种可能,即雄性小鼠通过某种形式将恐惧的信息传给雌性小鼠,雌性小鼠再通过某种形式传给后代。因此,“恐惧苯乙酮”这一信息就是编码在精子中,而精子中没有别的什么,无非就是一团DNA!
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同时也引出大量的问题。特别是:这种遗传的机制是什么?怎么可能以如此戏剧性的形式打破中心法则?研究者发现,因训练导致害怕这种气味的小鼠的大脑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与气味感知系统有关。与对照组相比,受训练小鼠脑中含有苯乙酮特异性气味受体的神经元数量显著增加,其后代中也是类似的情形。重复性的某种气味刺激会引起大脑中感知该气味的受体的变化,这不足为奇。让人费解的是,这一性状为什么会遗传给后代?这一信息怎么可能反向传给DNA?文章作者认为,真正受到影响的可能并不是DNA的序列,而是DNA上与某个特定基因是否转录有关的“记号”。这些“记号”可能通过DNA甲基化产生,即增加一个甲基到胞嘧啶或腺嘌呤上。一个特定基因的甲基化程度可能代表了该基因转录的重要性或优先级。目前已经研究清楚的是,胞嘧啶甲基化(通常是在基因上游的启动子区域)的增加会降低基因表达。关键在于这一信息可以在不改变DNA序列的前提下传递到DNA上。那么是不是有证据支持上述推测呢?实际上,雷斯勒和迪亚斯发现,苯乙酮敏感小鼠的精子里,苯乙酮气味受体基因上具有比对照组显著减少的甲基化记号。可能,这些甲基化记号的减少暗示该基因在发育过程中需要大量转录。
但是这个解释还有很多问题。首先,对刺激的恐惧反应是如何恰好改变了与那个刺激有关的基因的甲基化水平,特别是在精子中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一无所知。其次,假设甲基化的改变是做记号的方式,我们依然不知道这种甲基化的差异为什么或如何被解释成“害怕苯乙酮”的意思。例如,这为什么不是被解释成“嘿,这儿有好多美味的樱桃,闻到这个你应该非常高兴”?如果他们让另一组小鼠将同样的味道与愉悦联系起来,那真的会很有趣。这种反应也同样会遗传给后代吗?会产生同样的甲基化记号吗?而最有意思的可能是,如果他们让一只“恐惧”组的雌鼠与一只“愉悦”组的雄鼠交配,会有什么结果?这个研究引发的疑问肯定比回答的问题要多,但重要的是,它开始瓦解现代生物学中的一条核心法则。虽然我们还不知其所以然,但此研究表明中心法则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严格。
或许周太太是对的。可能她的祖母确实经历过与蜘蛛有关的恐怖的事,而这现在记录在她的DNA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大概是甲基化在她的DNA上产生了这个效果。他们的女儿也会怀有同样的恐惧吗?这还不知道,但是研究者们正在试图弄清对苯乙酮的恐惧会在小鼠中保持多少代。假如这真的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那么显然,我们的厌恶和恐惧可能是由以往经验的一个大杂烩决定的,而这一切来自于我们出生之前很久。我们真的可能是来自过去的一团恐惧。
(摘自《科学世界》2014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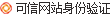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