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我作为项目最直接的见证人和最早的参与者,效力于西南种质资源库,业已九载。其间,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同仁,为了这项国家重大科学工程殚精竭虑、历经艰辛。每次忆及许多鲜活往事,都令人百感交集、心潮难平。
值此昆明植物研究所70周年所庆之际,我欲从建设种质资源库这座“诺亚方舟”的激流洪波中,采撷浪花几朵,以追忆那些逝去的难忘往昔。
一、朦胧方舟蓝图初现
事情得追溯到9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季。1999年7月,我前往美国圣路易斯参加第十六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借机顺访了哈佛大学、纽约植物园、加利福尼亚科学院等几个合作单位,还考察了加州与俄勒冈州交界地带的Siskiyous山区,于8月31日返回昆明。第二天上午,时差没倒过来,睡意朦胧的我,就接到昆明植物所计划处李正安处长的电话通知,要我当天下午两点赶到昆明分院开会。当我从黑龙潭赶到分院的临时办公地新迎小区的会场时,会议室内已有十余人。
据主持会议的分院张壮鑫院长介绍,吴征镒院士于8月8日向朱镕基总理写信,建议“尽快建立云南野生种质资源库”,朱总理迅即于8月15日作了批示:“我认为设想很好,应予支持”。云南省的主要领导和中科院路甬祥院长也分别指示,明确“种质资源库”工作由云南省科委和中科院昆明分院牵头组织落实。最后,张院长用简短而坚定的语气布置了任务,要求昆明植物所和分院的兄弟单位组织力量,与云南省有关单位一起,尽快提出一份建议书,供有关领导和专家研讨。
那天的参会人员,除分院和昆明植物所的有关负责人外,还有昆明动物所、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和云南省有关单位负责科研的领导和专业人员。其中,后来任种质资源库项目总工艺师的杨湘云博士,当时刚从英国学习种子生物学回来,她代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参加了会议,那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在同车回所的路上,李正安处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龙啊,我们作为植物所的人,对于吴先生提出的建议,一定要积极响应和落实,现在的任务是争取将这个大项目立项、得到国家的支持。我所从事生物多样性、种质资源方面的专家不多,我们请示了几位所领导,一致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一定要勇于挑起这副担子啊!”刚才的会议加上李处长的一席话,使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虽然我在1997年就被中科院特批为研究员,也成功申请并主持过一些重点项目,可项目所涉金额最多也不过百万元人民币,而该项目的投资将高达数亿甚至十亿(当时大家都这么推测)。如何着手申报如此特大型的超级项目,对于我也是个难度极大的新课题,我心里完全没有底,经过李处长再三强调,这才茫然地答应试试。同时,内心也涌动着一股前所未有的激情,仿佛激战前夕摩拳擦掌、随时待命的战士。
不到一星期,也就是9月6日的下午,由多个单位参加的研讨会在昆明植物所圆桌会议室召开(该会议室现已不复存在,位置在现在植物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南楼东侧)。参加会议的有当时的云南省科委(现为科学技术厅)、云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现为发改委)、云南大学、云南农业大学、西南林学院、中科院昆明分院、昆明植物所、昆明动物所、版纳植物园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和人员,昆明兴滇技术经济咨询公司也应邀派专人参会。
会上,我把几天来绞尽脑汁、悉心准备的十几页《云南野生种质资源库申请书》,用透明胶片通过投影仪放映在会议室粗糙的黄白色墙壁上,花了30多分钟向与会者汇报了申请书的主要内容。大家一致认为总体框架较好,目标和内容较合理,但仍需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修改、补充、完善,并进行细化。
会上,省科委的李村生助理巡视员(现已退休)、省计委高技术处的吴凡处长(后升任云南省发改委副主任、省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现任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昆明分院张壮鑫院长等领导,分别代表云南省和中科院讲话,并且在协商后研究决定:为落实朱总理的批示,要尽快组成项目工作班子,在云南省和中科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被任命为“前期工作组”组长。
我这个组长,当时被自己归纳为“三无”小组长,因为既无工作场所,也无工作人员,更无工作经费。但,有的是对国家种质资源安全负责、对科学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巨大使命感!
工作伊始,我们采取“游击战”、“运动战”、“流水战”(即人员流动性大、无固定工作场所、有时集中讨论有时昼夜奋战)的方式,联络、组织有关单位的人员,就各自熟悉的领域撰写相关章节、提供不同的专业资讯。大家分工协作,在总体框架内各自发挥。然后,由我根据情况进行取舍,反复修改,最终完成供领导和专家研讨的文稿已是若干个版本,厚厚的一摞。
这个时期,参加写作的人员涉及19个单位的30多位专家,其中较常参加写作的人员有:昆明植物所的王仲朗、张长芹、孙卫邦、杨祝良、曾英、胡虹,昆明动物所的李喜龙、向余劲攻、佴文惠,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杨湘云、施捍,云南省农科院的戴陆园、曾亚文、陈勇,云南省林科院的司马永康、施莹,云南省珍稀濒危植物引种繁育中心的欧阳志勤、张建邦,云南省微生物研究所的谷苏、陈有为,西南林学院的薛嘉榕、杜凡,云南农业大学的杨清辉、谢世清,云南省野生动物收容拯救中心的王安群,兴滇公司的张积寿、朱云华、陆晓玲。值得一提的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即北京植物所)的韩兴国所长和傅德志副所长还委派石雷博士两次专程赴滇,为前期写作工作出了不少好主意。
这期间,省科委的林文兰主任和李村生助理巡视员、省计委高技术处吴凡处长、分院张壮鑫院长、云南大学张克勤副校长等领导,不断敦促写作班子的工作,并组织省内有关专家对工作组完成的阶段性报告进行咨询和评议。
一个月来,经过众人集思广益,日夜奋战,我们为“方舟”绘制的宏伟蓝图已日见明晰:牢不可摧的库房、装备精良的实验室、琳琅满目的资源圃、郁郁葱葱的自然保护区,以及大漠深处的复份库……我们坚信,纵有狂风暴雨、巨浪洪波、这艘超级航母也将安然矗立、永不沉没!
二、结集“凤凰”精雕细刻
1999年10月7日,我接到通知去云南省委会议室直接向省委书记和省长汇报。当我小心翼翼地迈进会场,就感觉到一种特别的郑重氛围。只见当时的省委令狐安书记、李嘉廷省长,端坐于主席台上,会场内还有梁公卿副省长(后任省人大副主任)等一批省领导,以及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计委、财政厅、科委、林业厅、农业厅、环保局等单位的一把手。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在这么多高级别的领导中间,难免感觉有些紧张,好在头脑十分清醒!紧接着林文兰主任的汇报,我对相关技术要点进行了恰到好处的补充,条分缕析,看着令狐书记不住点头并投来赞许的目光,我虽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暗自欢欣!
在这次省委办公会议上,省科委提出需要省委、省政府解决200万元工作经费的请求,李嘉廷省长当即指示省财政厅安排100万元,用于种质资源库的前期工作。这笔经费由省科委掌握,具体由昆明兴滇技术经济咨询公司负责管理。
此后,我们大多数的统稿工作,都集中在位于北京路凤凰村兴滇公司二楼的会议室内进行。原本十分陌生的凤凰村,以及周围的大街小巷,因此渐渐变得熟悉而亲切起来。
我们写稿和统稿的具体做法是:根据每位专家的专长和背景,分配相应的撰稿或查找资料的任务,然后由几位骨干集中统稿和修改。参加统稿工作最多的是杨湘云、李喜龙、司马永康、曾亚文、朱云华、陆晓玲和我。通常我们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即集中讨论之后,打出一份稿子,每人顺序逐页阅读并修改,改完一页就传递给下一位,最后由我再看一遍。这种工作方法的好处是:能汇聚众人的智慧和力量,把握全文的结构和逻辑,认真规范每一处字符语句。由于各级领导对该项目都高度重视,不断组织各种形式的讨论、评审、检查、汇报,因此每次定稿都是临时决定,往往今天刚得到通知,明、后天就得拿出新版本来进行汇报,所以,为了赶稿夜以继日、苦熬通宵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从1999年9月到2001年8月,由于种质资源库项目以云南省为主、中科院配合,我们经常被召集到位于昆明市五华山的省政府开会。会议有时由梁公卿副省长主持,有时由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主持。当时的分管副秘书长有施天骏、宋玉麟,后来主要由钱恒义副秘书长负责。
1999年10月18日,施天骏副秘书长主持召开了主题为讨论成立“云南省野生种质资源库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的会议,会上商议由梁公卿副省长任组长,各相关单位(包括科技、计划、林业、农业、中科院昆明分院、动物所、植物所、版纳植物园、云大、世博园等)的主要负责人作为联席会议成员。考虑到当时任昆明植物所所长的郝小江研究员是位植化专家,我提议昆明植物所的联席会议成员由具有生物多样性专长的李德铢副所长担任,得到了会议的认可。该联席会议制度于次日由云南省政府发文确定。
2000年3月9日,云南省科委发文,成立了“中国云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保护研究基地”项目预可行性报告编写组,我被正式任命为组长,云南省微生物研究所(隶属于云南大学)姜成林教授、昆明兴滇技术经济咨询公司张积寿高级工程师担任副组长。
编写组完成的文本非常之多,我已记不清楚具体数目。仅2001年8月之前,我这里保留的不同版本就不下20个,包括:
1.“中国云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初步可行性方案》第一稿(1999年9月12日)
2.《“中国云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初步可行性方案》第二稿(1999年9月27日)
3.《“中国云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方案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1999年10月27日)
4.《云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方案》(讨论稿)(1999年12月13日)
5.《“中国云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2000年5月29日)
6.《“中国云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2000年6月6日)
7.《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中国云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项目建议书》(初稿)(2001年1月20日)
8.《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中国云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项目建议书》(2001年2月16日)
9.《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中国云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项目建议书》(收集、保存、研究、运行部分)(2001年3月8日)
10.《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项目建议书》(2001年5月12日)
其中,2000年11月20日之后,这些文本以“中计信工程咨询公司”(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脱钩出来的一个单位)和昆明兴滇咨询公司的名义编制,但实际工作仍由“编写组”来完成。
2001年,按照国家计委的意见,对项目名称进行了更改。2001年1月20日以后,名称被冠以“国家重大科学工程”;2001年3月9日以后,名称中的“云南”改为“西南”。在内容和经费预算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早期(2000年5月以前)的建设内容,包括了中心库(含信息中心)、其他地区复份库、种质圃、重点自然保护区、证据标本馆,是一艘系统、完备的现代“诺亚方舟”,总投资达11.38亿元,后核减为10.6236亿元。在体制上,这一“方舟”是个独立法人单位。后来不断调整,到2000年6月,总投资估算为6.9296亿元;2001年6月6日,为6.14亿元。2002年以后,建设内容仅包括原来的“中心库”,根据选址的不同,总投资分别为2.2765亿元(植物园方案)和2.28亿元(世博园方案)。根据国家计委对项目总经费和资金筹措方案的意见,2003年6月16日,海洋之神8590vip陈竺副院长(现任卫生部部长)与云南省政府陈小娅省长助理(后任教育部副部长)及有关领导在昆明进行了研讨,双方确认了1.48亿元的项目总经费,其中中科院投入12000万元,云南省投入2800万元。
在种质库的选址问题上,曾有几种不同考虑。起初,我们考虑在蓝龙潭与黑龙潭之间征用1200亩土地,那里是苗圃地,没有房屋等永久性设施,搬迁容易。后拟选择植物所以西、花园大道以东的地块(总面积300余亩)为库址(即“植物园方案”)。现在这其中南端和北端的两个地块被分别开发为“都市枫林”和“立欣洲”两个住宅小区。2002年,就种质库的选址,我们提出了两个方案,即“植物园方案”和“世博园方案”,后者的地址位于世博园东面的二期工程内,拟征用土地150亩、预留200亩。此外,我们还曾到原来的天成公司所在地了解过情况,该公司位于靠近茨坝镇(即现在的茨坝街道办事处)的花渔沟口,占地面积约600亩,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倒闭,经初步商谈,可以3000万元将土地转让给我们。2003年4月6日,中科院昆明分院经过向云南省人民政府请示,最终落实了种质库建设的用地问题,并倾向于植物园方案,计划征地150亩。最后,确定选择“植物园方案”中靠近标本馆的地块,向昆明官房公司茨坝分公司购买了80亩土地,用于种质库和昆明分院的建设。
三、往昔难忘逸事偶拾
1.“戴院长”痛失“坐骑”
2002年以前,私家车还很少。小组成员前往凤凰村或植物所集中写作和讨论时,路程远的坐公交,近的骑自行车,紧急加班时才坐出租车。
戴陆园研究员当时是位所级领导,李村生助巡喜欢戏称他为“戴院长”,我们大家也都跟着这样叫,也许是当时的称呼起了作用,“戴院长”后来正式担任了云南省农科院副院长。那时“戴院长”往来于凤凰村,总是足登一辆自行车,一路上骑得飞快,两耳生风。谁都看得出来,那辆车是他钟爱的坐骑。
有一天我们干完活已是半夜,下楼后,发现车没了!围着房子找了几圈也全无踪影,我们只有把该死的小偷大骂一通。我当时实在过意不去,便答应跟领导说说,从项目经费中给点补助。当然,我只是开了张空头支票,而“戴院长”也不会稀罕。令人遗憾的是:自那辆自行车丢失之后,“戴院长”开始慢慢发福了,真是罪过!
2.保全资料丢背包
又是一次加夜班,天快亮时才完成任务。我乘坐头班公交车,准备回家好生休息。可还没熬到半路,困得实在撑不住,就在座位上酣睡过去。等清醒过来,陡然发觉腰间的手机不翼而飞,只留下空空的皮套,仿佛在嘲笑我的疏忽大意。环顾车厢内稀稀落落的三两乘客,也都不似小偷模样,只好在心里大骂小偷几句。用当时两个月工资购买的手机,就这样与我不告而别。
这种蚀本买卖,我当时做了不少,但只是当时自认晦气,过后并无更多怨言。事实上,其他同仁也不乏类似遭遇。
一次,李喜龙博士(现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和我一同赴京汇报,他带的行李是一个背包。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症十分严重,就把那包重约8公斤的资料交他保管。下了飞机,已登上机场大巴准备去东便门附近的云南省驻京办,才发觉李博士只拿了那包资料,却忘了拿自己的行李。待他跳下车赶去“到达大厅”寻找时,哪里还有行李的踪影!那天我真是后悔莫及,若非因我腰痛难忍,便可随身携带那包材料,李博士何至于丢失自己的背包!
3.小娇女险遇不测
欧阳志勤高工,当年代表云南省环保局和珍稀濒危植物引种繁育中心,经常和我们一起夜以继日地加班写稿。记得那是一个周末,我又召集大家加班。欧阳把不满两岁的女儿玲玲交给外婆,就匆匆赶来。万没料到,忙于操持家务的外婆一不留神,身边年幼的孩子已不慎把一颗花生米呛进气管里!
心急如焚的外婆打电话催欧阳赶快回家,欧阳开始还没当回事,想把手头的工作完成再回去处理,直到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工作的孩子爸爸告诉她问题的严重性,欧阳这才又惊又急,大哭不已。等她火速赶到医院,看到自己的爱女小脸发紫,忍不住心如刀绞,泪水横流。当时医院已安排好手术,随时准备切开喉管取出肇事的花生米。幸运的是,就在手术即将开始前的十分钟,玲玲一声咳嗽,居然把气管中的花生米咳了出来!有惊无险,在场所有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如今,玲玲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漂亮小姑娘,像只小蝴蝶一般为大人们带来欢声笑语。爱美的她,如果当时在显眼处留下手术疤痕,伴随她终身的会是怎样一种痛苦?我不愿往下想,可每当看到她活泼可爱的身影,总有一种别样感受涌上心头。
4.风雨兼程赴北京
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还有一段特别的旅行。2001年5月18日上午,我正在云南最边远的贡山县出差,主要是在距离县城约6公里的当珠调查当地植物。突然接到通知,必须在20号前赶到北京汇报。当时的大(理)——保(山)高速公路、安(宁)——楚(雄)高速公路尚未通车,从贡山县城到昆明的直达车,要走两晚一天或两天一晚。当天的白班车已发车,我若坐夜班车,就可能无法赶上北京的汇报会。于是,我当机立断,准备采取分段赶路的办法,即从贡山到六库,从六库到大理(下关),再从大理到昆明。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在大理坐上飞机,能节省出好几个小时。
我立即从当珠的深山沟跑回县城,把行李胡乱一裹,就跑到县汽车站。幸好,赶上了中午从贡山县城开往六库的班车。在六库,也顺利接上了前往昆明的夜班车。汽车在黑暗中翻越了高黎贡山、跨过了澜沧江,在天亮之后进入永平县境内。可是,夜间的大雨,导致永平境内多处山体滑坡。在永平县和漾濞县之间的一座山丘上,我们前面的车辆,已经排出了长达十余里的长龙。望着车流一望无际、蜿蜒曲折的壮观景象,心情却异常沉重。此时前方却传来更坏的消息:山体滑坡致使汽车根本无法通行,大约要两天才能抢通。
沉吟片刻之后,我把心一横,卷起裤脚,决意步行。在路边停靠车辆中司机和乘客疑惑的目光中,我冒着毛毛细雨,在泥泞的路上艰难行进。在雨中行走开始还有微微凉意,后来却越来越感觉浑身发热。于是我脱下外衣,继续前行。不知何时,汗水和着雨水,将衣服完全浸湿;泥水,让裤腿满布污迹,但也没有放慢匆匆的步履。行至滑坡处,看到有辆汽车被埋了一半,幸而没有人员伤亡。过了滑坡处,侥幸上了一辆临时拉客的破旧小客车,终于在中午时分抵达下关。
顾不上吃一口东西,迅速赶往民航售票处,得到的却是机票已卖完的消息。又急忙赶往汽车站,跳上一辆正准备启程去昆明的依维柯,虽已座无虚席,还是暗自庆幸。坐在引擎盖上,将就近买的面包狼吞虎咽。一向不爱吃面包的我,却感觉车站小贩卖的面包格外香甜。
启程后我不断祈祷不要堵车,速速抵达。如我所愿,一路顺利平安,于下午6点多到达昆明。我从南窑汽车站一下车,就直奔昆明机场,只见妻子早已带着机票、皮鞋和换洗衣物,在候机厅焦急地等候。我在洗手间换了行头,一身光鲜地走进机场大厅。其时已过7点,但足以从容地赶上晚上8点起飞的航班。经过这段风雨兼程的不寻常旅程,我终于在20日上午准时出现在北京召开的工程评估会上。
四、秀才出招有谋亦勇
2003年8月中旬,中科院和云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发文,成立项目领导小组、项目管理委员会、项目工程指挥部。项目工程指挥部由李德铢任经理、甘烦远任副经理、龙春林任总工程师、杨湘云任总工艺师、胡斌任总经济师。就这样,一个大多由温文尔雅、书生气十足的“秀才”组成的工作班子算是正式搭建起来了。
在种质资源库主体工程开工之初,“秀才们”就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我看来,最难以攻克的,要数“征用‘三角地’”、“开通大门”、“军用通讯线迁移”、“高压线入地”等四大难题。
1、征用“三角地”
我们新征用的80亩土地,呈长方形,像一块大积木与昆明植物所原来的围墙镶嵌在一起。但是,在东南角,新征地和原来的围墙之间,包围了一块3.958亩的三角形土地,我们习惯地称之为“三角地”。这块土地在我们征用那80亩之后,成为了一块名符其实“飞地”,其所有者必须先从植物所的大门进入园区,然后才能到达三角地。为了消除这后患无穷的“园中园”、“国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征用它,使之成为植物所领地的一部分。
2004年的8月下旬做出这个决定之时,我正在云南省农业厅担任厅长助理(经选拔和院人事局的批准,我于2003年10月至2004年10月参加了中组部、团中央的“博士服务团”,任云南分团副团长,挂职于云南省农业厅),但这个光荣任务还是落到了我的肩上。经多方打听,三角地的主人是“官渡区房地产总公司(即官房集团)茨坝分公司”,以前的经理姓周,但刚换了岗位,新任经理姓张。我找到云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的周政总经济师,请他帮忙。周总不仅业务娴熟,而且为人豪爽、广交朋友,还是位摄影发烧友,在茨坝一带颇有威望。果然,不出5天,在周总的斡旋下,茨坝分公司的新老经理都聚集在镇上的一个小餐厅,围绕三角地摆开了“龙门阵”。经理们都比较懂行和敬业,先谈当前地价飞涨的大趋势,后诉三角地的重要性。
我的策略是:强调种质库项目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陈述三角地被包围和孤立后的诸多不便、历数早日出让给种质库的种种理由。我还利用当时担任农业厅厅长助理的身份,数十次找分公司及茨坝镇政府、和平村民委员会(主要是蒜村)的有关人员谈话、沟通,还通过昆明市有关部门施加影响。
新上任的张经理个子大,性子急,经不住我反复做工作,在请示相关领导后,与我们签订了“土地出让协议”。但是,在即将按照协议划拨经费时,张经理却与当时担任总经济师的胡斌发生了激烈争执,加之其他原因,三角地的征用进程一时受阻,双方陷入了僵局。经过多方协调,在搁浅近两个月后,我们终于成功征用了这片土地,使之成为种质库的有机组成。
在种质库的新征土地上,有20亩地用于中科院昆明分院修建新的办公楼,张壮鑫院长和贺开平主任(现任院长助理)也为前期工作付出了艰辛努力。
2.接通花园大道
就在种质库“三通一平”工程即将完成之际,2005年元月16日上午,负责该工程的茨坝建筑公司周经理急匆匆地在电话中向我报告:面向花园大道的出入口被蒜村的一些人用砂土和建筑材料阻挡,施工车辆无法进出,施工受阻。施工方与阻难方已发生口角冲突,随时可能导致械斗!我当时正在海埂参加科技厅的一个会议,立即从会场冲出来,电话要求施工单位务必克制、不可妄动,否则后果自负。在驱车赶赴事发地点的途中,又向有关领导汇报了相关情况。
到达施工出入口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简单的做法是指挥工人强行把障碍物清走,但有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而如果任其阻难,则有损于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尊严、滋长歪风邪气。两种思想在不断斗争,相持不下。最终,在农业厅的任职经历帮助了我,我慢慢冷静下来,立即前往茨坝镇政府(其时已更名为茨坝街道办事处),请他们协调解决。在办事处主要领导的协调下,双方的冲突终于被制止,“三通一平”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然而,好景不长。3月6日中午时分,主体工程施工人员在花园大道出入口运送建筑材料时,又遇到了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和平居委会(即蒜村)部分村民的强行阻挠。他们用车载来了几十人,开来推土机等大型机械,把新开口处的铁大门和原来出入口的大门强行拆除并拉走,运来垃圾土和直径达1.5米的巨型下水道水泥管,把两个开口围得水泄不通,施工无法开展。施工人员和阻挠人员正在紧张对峙,一时间剑拔弩张,情势十分危急!
我在第一时间赶赴工地,稳定现场人员的情绪,并立即电话联系茨坝办事处的主要领导,然后向110报警。所领导和有关人员也出动,希望能尽快解决争端。人员虽然很快疏散,但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反复找茨坝办事处,也没有结果,后来有关人员干脆借故不见;向省政府打报告,请求有关部门解决,也未果。
为何蒜村村民会有多次过激行为?后来经了解,才知道事出有因。原来官房集团在花园大道(当时只是一条规划中的道路)以西购买土地时,支付了部分资金修建花园大道,他们在与茨坝镇政府签订土地转让的合同中,明确其有权在花园大道开口。我们认为:从官房集团征用土地后,我们也就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在花园大道开口的权利。花园大道由官渡区交通局、茨坝镇政府与官房集团等单位共同出资修建,镇政府是主持单位。在镇政府与当地村社签的协议中,明确道路的产权不变,镇政府只付给每亩一万元的青苗补偿费。也就是说,村民们仍对其土地(尽管变成了公路或街道)拥有主权。矛盾由此产生:我们有理由在道路上开口,村民们也有理由保护自己的权益。问题出在镇政府当时没把事情办妥,且其领导换了好几茬,谁也拿不出足够的土地补偿金,怎么办?
此时,张壮鑫院长表现出作为决策者的果断与机智。他提议先在靠近标本馆的围墙这边开口,急需的建材和物资从所大门进入后经此口运进工地;对于在花园大道上开口的问题,在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尽快协商解决。他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正、副经理也认为这是比较理想的解决办法。项目部委派胡斌和我负责与蒜村谈判,尽快解决在花园大道开口这个疑难问题。
经过胡斌、我、还有植物园李云等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和蒜村达成协议。而且,应了那句俗话:不打不相识。尽管蒜村和我们仅一墙之隔,但平素交往甚少,有时仍为一些事闹得矛盾重重。如今,双方在有重要活动时,都会请对方参加。我跟他们当中许多人还成了朋友。
3.通讯线路迁移
在种质库园区上空,有不少电线纵横交错,密如蛛网。为了安全、施工便利和日后管理,必须对这些“蜘蛛网”进行妥善处置。其中,最困难的莫过于军用通讯线和三路高压电线。
当时,军用通讯线贯穿种质库园区的东部,即靠近植物所原来的围墙,无法移开,只能入地。经与负责该线路管理的解放军某部取得联系后,请他们出具方案、根据方案做出预算。虽然,此前我们根据材料、工艺等也进行了较合理的估测,但对方的预算超出我们估算的好几倍!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怎么办?我们不能随便移动军事设施,必须由他们自行施工;但我们的资金有限,又必须合理使用。如何说服对方,在相对合理的资金范围内,尽快完成设计和施工,成了我那时的首要任务。
谈判,许多次的谈判,没有结果。想办法,出主意,还是行不通。所长郝小江研究员与部队政委一同参加过政协会议,于是他请求政委出面协调,虽然有所进展,但仍然未形成我们期望的“理想合作关系”。副所长李德铢研究员多次参与谈判,他的岳父是军界前辈,这层关系使双方拉近了不少距离,但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
雪上加霜的是,在谈判稍有进展之时,军用通讯线经过植物园裸子植物区上空的一根电线坠地,对方怀疑是我们不满他们的谈判结果而有意所为。我立即赶赴现场查看,经过多方核实,三天后查清了事故真相,也取得了对方的信任。
对方负责技术工作的罗工为人忠厚,作风踏实,我经常利用休息时间与他交往,增进了解。负责谈判的参谋长是云南某县人,聪明善言,热爱家乡,我有意让他的小同乡——我的一位研究生与他交流。有时候,谈判结束得很晚,准备工作餐时,我就请来自己的研究生帮忙。他们以自己的机智和纯朴,巧妙地表达了我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不折不扣的财务制度,促进了军方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认同。这期间,我所的甘烦远主任(兼任副经理、现任副所长)也为谈判的成功付出了许多时间和心血。王红、马晓青、邹军武、周翊兰、罗吉凤等,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历大半年的谈判之后,双方于2004年底达成了协议。工程款支付之后,他们便以军人的速度,很快完成了军用通讯线路的入地工作。只是,我欠下了他们两个很大的人情:一是答应在种质库大楼竣工验收时请他们出席仪式,因故未能如愿;二是给勤奋好学的战士们提供一个机会,到西双版纳植物园接受科普教育,亦未能成行,两个未能兑现的诺言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4.三路高压线入地
工地上方有高压线通过,而且有三路!在主体工程不断向前推进时,来自空中高压线的威胁却越来越大。其中有一路高压线正好从主体工程的西南角上方跨过。当时,高压线的“迁杆移线”问题已迫在眉睫,必须立即解决。
其实,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从项目开工时就被提了出来,而且在项目领导小组会上讨论过,贺开平主任也就此事专门找昆明市供电局的书记谈过,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原因很多,涉及到市供电局、负责北部地区供电的东城分局、设计单位和具体的施工单位等,大家都表示尽快办,但真正推动起来却很难。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各地的供电局是个特权部门,要找他们办成事绝不容易。这个艰巨的任务,又一次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理了一下头绪,先对问题进行仔细梳理,认为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具体落实该工程的施工负责人身上。他们同时应对许多工程,而每项工程都有时限,谁盯得紧一些,谁的工程进度就快一些。而具体管理施工负责人的部门,是昆明市供电局东城分局的计生室。原因找到了,遂设法解决。
参加种质库项目前期写作班子的欧阳志勤高工,其胞妹欧阳志红恰是市供电局的一位部门负责人。我们通过她与东城分局计生室的范主任取得了联系。可范主任很忙,经常开会、出差和下工地。于是我采取了“围追堵截”的战术,不解决问题誓不罢休。有时候是独自一人,有时候带领杨志华、贺伟、现场代表石章福,在他们办公楼的走道或者办公室里等待。用杨志华的话说,堂堂中科院的教授,下这么大功夫等一位科级干部,实属难得,诚心可鉴。而我却认为,只要能尽快把高压线移入地下、推动工程进度,这样做完全值得。在高压线入地的施工过程中,不断出现一些问题,我总是亲自出面请范主任解决。范主任的下属黄其兵工程师和陈渝云工程师,也为此经常享受这种被“堵”的待遇。
另外,我对施工单位也盯得很紧。施工方的两位主要负责人,恰巧和我住在同一小区,而且我们的车库还紧挨在一起。这样,每次见面我都要追问打听,有时还约他们在附近的茶馆谈谈工程进度以及存在问题。
就这样,繁杂的“迁杆移线”难题,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最终被一举攻克。在此,我要真诚感谢协助我工作的项目部人员:欧阳志红主任、范伟主任、黄其兵和陈渝云两位工程师,以及江南和唐骏两位施工负责人。
五、绿海扬帆方舟远航
经过八年多的艰辛努力,西南种质资源库这座“诺亚方舟”终于打造成型,在我国西南之隅傲然矗立,引起了业内外的极大关注和普遍赞誉。种质资源库主体工程于2007年2月8日通过了竣工验收,同年的4月29日还举行了盛大的剪彩及揭牌仪式。种质库自建成至今,业已成功运行,初步发挥了既定的重要功用。该工程的建成,还入选了2007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科院和云南省的领导、国内外知名人士已多次视察、参观种质库工程,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璀璨的光环背后,是艰辛的付出,是默默的奉献,是永恒的挂牵。
作为种质库建设项目的直接见证人和主要参与者,我衷心期待种质资源库在未来的日子里,遵循吴先生的思想,沿着精心设计的“航线”,稳步向前,成为“亚洲一流、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野生植物种质资源保存与研究服务基地”,成为浩瀚的植物世界中永不沉没的“诺亚方舟”,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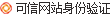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