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长,人生短。我像流水中的一株小树,没有顺流而下,而是留在了流经的小潭中。昆明黑龙潭畔我留下了;没有完全枯萎,也未成大树;有了家庭,有了后代;结识了前辈,相交了同辈,教出了后辈;有苦有乐。能活到今天,活到八十岁,可谓幸事。
云南有很多龙潭,白的蓝的黑的都有,称黑龙潭的我就去过三处,云南丽江黑龙潭,嵩明白邑黑龙潭,两处也很美,最美是昆明北郊黑龙潭。据《汉书,地理志》和东晋《华阳国志》,黑龙潭即黑水池,这是地方史专家任乃强先生考证出来的,似属可信。有唐梅、宋柏、明茶、元衫为佐证。唐梅死于清末,但碑刻犹存,元衫即柳衫,死于七十年代是我亲见。黑龙潭后山是五老峰,建成二百多亩梅园,冬末春初最早开花,比江南早两个月,红梅、白梅有百余品种,我最爱绿萼梅,他处少见。黑龙潭隔壁有昆明植物所的茶花园,园里还有樱花和木兰,浓浓春色从黑龙潭开始,稍后其他公园的花也陆续盛开,形成了“园林处处红云岛”(杨慎:月节词)的花潮。
黑龙潭畔有一个元宝山,这就是昆明植物所前身云南农林植物所所在地,更了几次名,现名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景色宜人。据说风水也好,云南的头面人物龙云生前选的墓地就是元宝山,他早死的小儿子和他的岳父一葬元宝山,一葬黑龙潭。云南最早革命先烈也立碑黑龙潭。抗日时期科学院前身之一北平研究院也暂住元宝山。站在元宝山最高处昆明植物所标本馆一侧,可远眺滇池,睡美人历历在目。云烟大金元也是在元宝山由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我的老领导后称蔡老的蔡希陶教授首先引种推广。昆明植物所在七十年代前远离主城区,干扰少,是做学问的好地方。
偶然中的幸运
一九五八年我从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制药工程专业毕业,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到校找我谈话,要我到中组部报到。我说家庭出身不好,不适合,他们觉得也是。后来我选择了昆明,那时只知道昆明四季如春,不知一雨成冬。我除抱着建设边疆愿望外,实际上还有一个至今才敢用文字表达的私愿,就是远离我国政治热点地区京、沪。九月份踏上了由上海到昆明的道路,先坐火车到贵州都匀,等了两天才买到去贵阳的汽车票,到贵阳后我和好同学黄以诚分别,去年她已仙逝,感伤得很。在贵阳等了两天才买到去云南沾益的汽车票,再坐火车到昆明,历时十天。到昆明又等分配,后要我到中科院云南分院筹备组段亚华同志处报到,她告诉我你将分到准备筹建的化学所工作,现先寄放在植物所昆明工作站植物资源化学组工作。这一研究组在新建的一幢楼,这一幢楼是蔡老和彭加木先生指导设计建造的,蔡和彭又从云师大请来留美的蔡宪元先生到组上工作,彭先生还从北京科学院仓库中搜来旋光仪和熔点测定仪等设备。蔡老早已经仙逝,彭先生也在罗布泊考察中不幸葬身沙漠。创业难,首创之功,我们将永远铭记。
我到工作站报到是在中秋前夕,中秋晚上冯国楣先生代表工会举行欢迎会,讲了话。吃的还可以,不记得有今天很常见的月饼,会后回到现茶花园,原农林所的老办公室。新来的男女同志各住一间统铺,晚上听到黑龙潭对歌,听不懂,有趣,或许是今天说的原生态吧。过了几天见到蔡老,他就不让我走了,我留下来虽属偶然,历经折腾,总体上是幸运的。
大跃进的折腾
来站不久,发了我一把锄头和镰刀,先参加冯耀宗同志指导的香叶天竺葵丰产试验,后参加同年来的张敖罗同志指导的蓝龙潭后面的小麦亩产5万斤的放卫星试验田。放卫星当时我是相信的,因为来昆路上从报上看了一张小孩子坐在稻穗上的照片,所以搞卫星田,我算卖力。后来蓝龙潭的卫星田不了了之,国内其他地区也失败了。今天也有人常说失败是交学费,吸取教训就好,可怕的是不认输。
到了资源化学组,已有两个小组,一是蔡宪元、卢人道的芳香油小组,一是杨希云的油脂组,我向蔡老说我想搞药,搞药用植物资源化学,蔡老同意了,不久蔡老任命我为室秘书。
1959年初由科学院裴丽生秘书长主持,在京开了植物学工作会议,由蔡希陶和浦代英带我参加,当时蔡和浦是植物所昆明工作站的主任和副主任,工作会议上讨论的问题较多。有一个问题是粮食多了怎么办,大家意见是搞大地园林化。最近才知道这话是有来头的,是毛主席一次参观展览会时提出的(见2011年3期《科学新闻》)历史证明,当时粮食不是多了,而是不够吃。参加这次会议我记得的有秦仁昌、裴鑑、朱济凡、曾呈奎等。会议进行中有一位穿着长袍的长者直奔主席台,台上就坐的蔡老等都起立让座,老者上台就讲,大意是经济植物资源很重要,蔡希陶在云南搞的就不错。此人是谁,就是毛主席称为生物界老祖宗的胡先骕。整个会议,我们小字辈的都是“旁听生”。 这年4月科学院批准建立昆明植物所,著名植物学家学部委员我的长期领导现称为吴老的吴征镒任所长,蔡、浦为副所长。
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利用和收集野生植物原料的指示》。昆明和北京植物所组织了云贵两省的经济植物普查。我室聂瑞麟参加丽江,丁靖垲参加黔东北,我参加黔南和黔东南。我们都用设计的野外植化测试箱进行简单测试。我是第一次接触西南野生植物,张永田是队长,老专家是匡可任先生。在那里我和匡老结成了忘年交。这时贵州已呈现粮荒现象,伙食不好,匡老生病,我劝他回京。临走时他瞩咐我一定要提醒张永田在黔东南採马尾树标本,果然採到了,我野外简单发现此植物树皮含鞣质较高,匡后来为马尾树作了深入研究并发表论文。在黔南罗甸县完成任务后转赴黔东南雷山县,到凯里和雷山时,州县领导都说雷山森林很可怕,毒蛇咬死过地质队的人,我们毅然去了雷山,毒蛇未遇到,但认识了少数民族苗族,那是一个善良可爱的民族,路上遇到,都问我们“大哥哪里去”,晚上苗族小伙子在村寨一幢公用竹楼对歌,然后成双成对的到外边谈恋爱,自由恋爱是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比汉族好。雷山生活也苦,采标本路上都需要采一些蕨菜回来当菜吃,餐餐如此,可见大跃进已跃得很穷。
在罗甸和雷山找到的经济植物有艾纳香(当地生产冰片)、地坛香(白株,芳香油主含水杨酸甲酯)和雷山大百合(荞麦叶贝母,后来知道云南用全果代马兜铃)等十余种植物,我学植物从此时开始。
回到昆明后,中科院有机化学所派了姚介兴和陈耀焕二同志来昆合作,算是和有机所合作的良好开端。后来我又到有机所请来了孙朗乾和俞晓峰,建立了玻璃灯工房。孙走后,俞晓峰长留了,不仅会做一般玻璃仪器,还能做磨口仪器,是当时云南第一家。室里人人求他,蔡宪元戏称他为俞老爷,后来也有人跟着叫,实际上他是全室最年轻的小伙子。姚介兴在所期间的一次党小组会上,谈到大跃进,他说可能毛主席也有责任,我附和了几句。姚走后,不久反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分院重点是蔡希陶和段亚华,我是所重点,在一次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上,作了“深刻”检讨,一次过关,大概中央和省里也不想扩大化。
1960年夏院领导张劲夫来所视察,在所主楼贵宾室用水果招待,他要我们搞代食品,他回到北京后批评了我所,所里马上行动。木全章和翟苹去武定搞橡子,我带夏丽芳、白佩玉、吕正伟去大理不仅搞橡子还搞小球藻、叶蛋白等。在祥云我亲眼看到了人们营养不良的现实,我也得了浮肿病。有了反右倾挨批的教训,不愿说,也不敢说,不久代食品也不了了之。
我爱动笔,政治不敢多讲,学术还兴百家争鸣,于是我写了“鞣质在中国山毛榉科的分布规律”,以周俊、冯国楣、木全章名义公开发表于《云南学术研究》5期。以后由我组织了冯国楣、唐耀等人写成《橡子》一书,由周俊、冯国楣主编,交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那次代食品运动,未查到有人出书,我算有所表现,在同年来的大学生中唯一被批准为助理研究员,那时是稀奇的。后来又写薯蓣皂素在薯蓣属的分布规律,明确指出根茎组是薯蓣皂素(diosgenin)含量最高也是最有希望的一组,后来我的化学研究完全证实。蔡宪元也写樟油成分在樟科分布规律的论文,交吴老在上海有机化学所的植物资源化学会上代为宣读。
1963年初,所里开了一次所务扩大会议,那次会议是在尚未度过人为加重的自然灾害情况下召开的。1959年蔡老以主要精力建立西双版纳植物园,那里实行一杆子方针,即一项任务各学科都上,直至生产推广,所里实行吴老半杆子方针,即建设和发展学科,生产任务由各学科根据自己情况参加。那时科学院也有学科带任务和任务带学科的争论,现在看是很正常的争论,没有谁对谁不对的问题,在那个提倡“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就算有争论。行政上也有晋绍武和浦代英之间“班长”和分管行政副所长的职权之争论。参加会议的有所领导和中层干部,中层干部看法也不尽相同,因为我和各位所领导关系都不错,被指定为会议秘书,我又请了武素功和杨崇仁两位同志作记录。吴老作了“三个战场,八大兵种”口头发言,三个战场指丽江、版纳、昆明三个植物园。八个兵种指分类、植化、生理、土壤、植被、微生物、引种、驯化等学科。蔡老作了植物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发言,会议开的很热烈,讨论也自由,我则在各领导之间协调。会议已开了十来天,决定结束。我用了一天一晚的时间写成“会议纪要”,领导一致通过,由吴老向与会干部和所部同志传达。纪要写的办所方针是“我所要在毛泽东光辉思想照耀下,形成花开三带,果结八方,群芳争妍,万紫千红的局面。”实质是昆明搞半杆子,版纳搞一杆子,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后来在文革中被批为修正主义黑纲领,吴老在批斗会上承担了责任,他说:“纪要不是我写的,但我是同意的,纪要是我宣读的,我负责。”在后来的小型批判会上,大家知道是我写的,就批我,我说不是写着“在毛泽东光辉思想照耀下”吗,造反派说“那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扛红旗是造反派的专利,我能说什么呢!反正白旗、白专扛了多年,黑旗也不在乎了。
文化大革命的往事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已有结论,无须我叙述,也叙述不好。只好谈一点我所特别是我个人的遭遇。
我个人认为“四清运动”不无可能是文革的前奏,1965年5月我有幸参加首批云南大理市的四清运动,开始说农村干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后来又变成查农村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运动。我参加了洱海东面康朗公社四清。我负责生产四队,按王光美同志桃园经验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后不问青红皂白先夺生产队长的权,请他“上楼”,折腾了两个月,没有发现生产队长有什么经济问题,经过请示同意,让他成了公社第一个洗澡下楼的生产队长。我本想清闲一下,此时其他生产队还在热火朝天的开展大揭发,越揭越多,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因为年底运动完不成,工作队就走不了,于是大队里调我当文书,我请各工作队员写了各自生产队的问题,再找各生产队长谈问题,听了他们申诉,一个队长也就一两个小问题,建议他做一个检讨下楼。公社书记则有四十多条问题,我听申诉后落实的也就四,五条,主要是生活作风问题和一小点经济问题。用今天标准看,算是廉洁或基本廉洁的干部。他的处分是工作队和分团领导的事,反正不轻。四清运动就是一个说不清的运动,可能是中央一两个领导人出现分歧,因为清查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是第一次提出,1966年5月的文革,其主要目的也是抓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因而说四清是文革前奏,有这种可能。总之四清运动伤了农村干部的心,浪费了我们的青春。
在“四清”运动以前和以后我认真做了点植物化学研究,先前还跟吴老和云南大学朱彦丞带领我所和云大部分同志参加文山西畤法斗和麻栗坡的植物采集,加上以前匡可任先生和这次吴老的指点,我开始懂得了一些认植物的知识。
1966年5月16日我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云南八月份进入了高潮,所里的重点是浦、吴、蔡、(晋已调动物所),浦是邓小平同志的大姨子,这次有幸名列榜首,张敖罗和我是走资派的红人和修正主义苗子,少不了要奉陪,城里游街,所里也跟上。一次所内游街,王庸充当了马前卒在前面敲锣,浦、吴、蔡头顶高帽,胸挂黑牌,手摇小旗,高唤打到自己,张敖罗紧跟其后,面带微笑,被一个造反派发现了,说他不是好东西,就赏了一顶高帽子。我是低头微笑,虽未被发现,有人说我也不是好东西,帽子准备不够,就赏了一块黑牌子。平时是半天去水生区种菜,半天在已拆掉的植化室小房子写大字报,写请罪书,批判会常常上演,浦、吴、蔡是主角,张、周、唐燿是配角。我挨打两次,一次是陪斗时头低的不够被打了狗头,后来又被打了一次头,都是高高举起,轻轻打下,挨打最厉害的是浦代英和唐燿,唐因为没有喊某某万岁,我下来问他为什么不喊?他说人怎能活到万岁。他不懂这是历朝历代留下的崇高称号,文革除四旧,万岁是不能除的。此外也保留了一些“四旧”,逃过四旧的文物古玩今天成了宝贝,四书五经、历史、文学、小说也未除尽,这样今天才有古书可读。文革抄家盛行,我因早有准备,笔记和书信都烧了,什么也没抄到,文革遗物,我仅有贴我的三百多张大字报摘要,留作纪念,一份不想看的纪念品。
文革中云南有“八二三”和“炮兵团”在城里武斗,我所元宝山也有真枪实弹的武斗,我所造反派战术逃退,我们这些被斗者,自愿留下保所,李楠、张斌是我们的领导者。
文革中我受的苦和我爱人陈泗英比算是轻的。我和她谈恋爱,历时九年。我们先后参加抗美援朝,她在上甘岭二线医院工作近一年。后来我在上海读大学,两年后她在南京读大学。1960年她才分到昆明的云南省药检所。结婚后生了大女儿周云,云南文革开始不久,她生了二女儿周露,那时周云才三岁半,便送在幼儿园。一天一个药检所的造反派坏头头胡编了一句周云在幼儿园骂毛主席的天大谎话,按造反派的逻辑是妈妈教的,于是才生完孩子12天的陈泗英成了现行反革命。挨批斗其惨状现在年轻人无法理解。当时传达了中央大人物的一句拗口话“文化大革命是革那个革了别人命的革命运动”,用现在考大学语文评分标准,可能比白卷英雄辽宁张铁生的分数高一点。不久某些领导人按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进行下放,陈泗英下放到曲靖,幸亏保姆张奶奶愿意同去,我和陈泗英不时在昆曲间短期走动,不久又生了周霁。陈泗英忙于县医院药房工作,幸亏有奶奶带,带了半年多,奶奶把儿子带去老昆曲公路旁小哨,约有半年,这世界还是好人多。陈泗英又由好人帮忙调到昆明植物所,我才去小哨将儿子接回,算是两代人大团圆。
文革中,还搞了一次谭甫仁的划线站队,站错队的关大牛棚,被戴白袖套,边劳动边交待揭发,我因工宣队要搞桑色素献礼,全所只有我学过化工,勒令参加加工厂内部设备和管道设计,没有享受大牛棚的待遇,在那里很多人挨了打。
文革后期还做了一小点研究,我写了提纲,杨崇仁完成全文,就是后来发表在《植物分类学报》上的“从植物化学成分的比较看单子叶植物起源问题”,1975年吴老已“解放”可以做研究,我和伍明珠研究了人参三萜化学成分,杨崇仁整理了人参标本,最后是我和吴老合作写成了“人参属植物的三萜成分和分类系统地理分布的关系”,在1975年《植物分类学报》上发表。值得一提的假人参是从北京植物所借来的一份西藏聂拉木标本根部背面取的植物样品,仅有34毫克,化学工作做的十分小心。天麻的化学成分研究,也是由我、杨雁宾、杨崇仁等在文革后期开始的。十年文革就做了这点研究。
文革十年还有不少事可写,但文革在历史长河中也仅是一瞬,我们所和我个人也仅是边疆一个小角落和一个小人物,让一切都如烟飞散吧。
黑龙潭畔春长在
1976年10月6日北京粉碎了“四人帮”,那时孙汉董、林中文和我在河南开封,调查抗食道癌药物冬凌草,孙、林重复在昆试验,分到冬凌草素,有抗癌活性,“四人帮”毒瘤粉碎,喜事,街上人山人海欢庆,可见文革和“四人帮”不得人心。
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党中央的领导职务,他花大力气管科研,说“愿当科研的后勤部长”这年10月海洋之神8590vip为主,发起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自然科学规划会议。吴老带了我,蔡老带了许再富,科学界很多老先生都参加了,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志指示,10月24日中央领导还和与会者合影留念。在生物学大组上指定邹承鲁先生为秘书长,我是两秘书之一,会议开得空前热烈,有些老先生争论得拍了桌子,这种自由学术争论,就我一生所见,可算绝后。这次会上我提出要把植物化学作为学科,生化所王应睐首先支持,大家也支持。有些要成立学科,未获支持。会上还承认云南生物资源丰富的地位,建议成立很多研究所。吴老会下向我说了一句话,不管成立多少研究所,我们两个研究室不能分,我说好。在这次会议进行中,蔡老首次突发中风疾病,送医院治疗,用了很多药,我记得的有天麻钩藤饮。说是突发中风,其实也非突发,在版纳受了挨斗的各种“酷刑”,不是积劳成疾,是积“斗”成疾。加之他是闲不住的人,仍然要把文章写在大地上,很可惜没能活到更长的高寿。
1978年5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会上华国锋做了报告,谈的很泛,虽无不当,但未受重视。讨论最热烈的是小平同志的报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高度赞扬了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刻苦劳动,对科研人员提出多条殷切希望。有人说小平同志把我们想说的都说了,没有想到的也说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老已经病重,开幕式中途退席,但播音员朗诵了他诗一样的发言“科学的春天”,我有幸参加,吴老三兄弟全部参加,互用古诗唱和,登载于会议简报,成为佳话。回到昆明,在机场通知我晋升副研究员,又抢了同年来昆诸同志头名。
发展科学离不了人才的培养。日本大鹏药厂领导组团来中国寻求合作,首选云南,随行翻译矶公昭是曾受我党培养再返回日本的中年。参观过程中我向他们提出由大鹏药厂资助,我方派两个人去日本大学读学位。团长说他可以当场决定,你们中国方面不能吧。我因为事先和生物局领导宋振能同志通了电话,他授权我全权决定,于是回答说我也能,双方击掌为凭,接着就送了孙汉董、杨崇仁赴德岛大学学习。此时我和广岛大学田中治先生已通过写信和寄送纯化的样品合作研究三七。这样田中治又找到广岛涌永药厂资助,杨转到广岛大学田中治处读学位,接着又派了丁靖凯、聂瑞麟去他那里学习,后来经田中治介绍认识了京都大学藤田荣一这一日本药学界前辈,于是又派了郝小江去京都大学富士薰先生处读学位。起初想要他做小红参的植化工作,不久改学天然产物合成,现在看来也是明智之举。张壮鑫去了北海道大学三桥博教授处继续研究C21甾体配糖体,吴大刚则送德国留学,后来陈纪军也赴日留学等等。我算尽了一点微薄之力。
先进设备、现代化仪器也是科研工作不可或缺的,具体购买考量过程实际是从1975年开始的。那时,我刚“解放”,不能完全看懂外国植化论文,外国人用核磁,几张图就把化学结构定出来。国内长春应用化学所和上海有机化学所虽然有核磁,但未带傅里叶变换,不能做碳谱。此时瑞士Bruker在北京展览FT-90,于是决定购买,而且一买就买先进的。那时昆明植物所还属省管,就要到省里批外汇批钱,故先找老首长省革委会文卫组副主任刘希玲同志。他问需要不需要,我说需要;又问会不会用,我说保证学会,于是他当即同意。随后又去找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由李楠和我找了生产组阴同志代转请批,也是立即批下。就这样,购置了国内第一批参展的两台FT-90核磁共振仪中的一台。这台仪器由王德祖同志专管,管得好,作用也大。后来趁方毅视察我所机会,又向他要来了GC-MS(气-质联用仪),再后来又和日本山之内制药厂合作,得到三年300万美元每年100万美元的经费,我方提供植物提取物,上海药物所也参与合作,这在当时是笔大经费,我所大型仪器和常规仪器如旋转蒸发仪都进行了更新。
有了人有了仪器还想要名。1987年我们研究室申请成为中科院植物化学开放研究室,不是科学院最早也是较早,不久在成都进行开放实验室评比,我和杨崇仁等三人用投影仪汇报,投影仪当时属先进设备。我室除工作成绩外,重点是我室送外国培养人员全部回国,别的所做不到。因而我室进入前三名。后来国家发改委科技司决定成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当时孙汉董是所长,正逢出国,请来评委,我作了长篇申请报告,出席的评委同意了,不料又遇到了较多周折。不久国家重点实验室改由科技部管,又重新申报。评委会上我说不评上国家重点实验室死不暝目。科技部程津培副部长分管国家重点实验室,他要将原植物化学开放实验室改为跨学科的西部植物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小江请人沟通,未获满意答复。于是我又请当时的白春礼副院长向程津培沟通,这就有了植物化学和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一国家重点实验室来之不易,值得珍惜,值得全室同志在所领导和室领导带领下使科研工作更上一层楼。
1989年6月4日前,五四青年节前北京已传来一些错误信息。于是我召集青年人开会,我说上街不行,其他均可以。他们说去澄江,我问要多少钱,他们说500元,我说不够,带1000元。我电话请求澄江县领导,准备了丰盛的午餐。青年学生玩的高兴,吃不完他们还带回一些,这就纪念了那年五四。五四后大概是五月八日我经北京到青岛中科院疗养院享受生平第一次疗养,在青岛从电视中看到北京等地学生游行情况,于是在5月28日离青岛去沪,又转赴南京,和南京老友尹宗清交换了看法,6月1日我由南京飞昆,在家休息了两天,实际上也顺带了解所内动向。6月4日中央对这次风波定了性,于是5日早上去所部召集中层以上干部开会,宣布六条纪律。中心是即日起不准再参加社会上任何活动,对所内张贴的北京来的宣传品,要一撕二堵;所内各部门要管好自己人,有情况要立即汇报。后来又召集了一次青年学生的会,我作了约一个半小时的长篇口头发言,大意是我是参加和搞过学生运动的过来人,请大家听我劝告,您们中一些人坐着贴有“海洋之神8590vip”大标语的汽车,进了城游行,据说拍了电视,我知道有些不是电视台拍的,你们不了解情况就算了,我作为法人代表,我政治觉悟不高,我负责。大家按省委规定学习七天,手头的研究要继续进行。我清楚记得我讲话的结束语:我是过来人,经历过风风雨雨,而您们可要警惕啊!
我是党委委员,在党委会上,我明确提出,不要再上报任何材料。总之六四期间,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不管哪种表现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我则是尽一切可能保护青年人。上级也来所追查过一次,我是环顾左右而言他。有次省委宣传部通知“共和国卫士”来所,要我组织人欢迎,我想所里围观的人肯定不少,不必组织,“共和国卫士”不就是解放军吗。于是我带头高喊“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接着我又请办公室带他们参观温室。各送鲜花一束,皆大欢喜,我所“六•四”最后也是皆大欢喜。
1990年考虑到当所长总要影响科研,同时所里基建财务也出了一点问题,因而辞去了所长职务。在90年前后也带出来一些研究生如张壮鑫、邱芳龙、郝小江、李春葆、蒋子华、邱声祥、陈纪军、邹澄、魏孝义、谭宁华、张荣平、赵玉瑞、丁中涛、汪有初、程永现、戴好富、邓世明、赵友兴、贾爱群、李宁、华燕、王利勤、吴颖瑞、胡江苗等二十名,他们的学问是自己苦出来的,成就也各有千秋。当室主任时是秦润宝代管后勤,现在是刘玉清为我负责组上行政管理。
总结五十三年,做研究最多三十五年,有一些成绩,另文介绍。我自己有很多毛病,最大的毛病是骄傲自大,想夹着尾巴做人,但本性难改。浦代英在一次会上批评“植化室上至周俊,下至俞晓峰都是尾巴翘到天上的人”,可谓中肯。不当所长后,得到所里同志的评价是“做了许多好事,没有整人。”这是不少老同志说的。仅此评价,我已愧不敢当。
八十岁了,体弱多病。科研上有些想法,提出来由别人做,自己也指导为数很少的学生做一点,仅此而已,谈不上今后设想。
黑龙潭畔情长久,岁月催人老,情多久,天知道。
周 俊
2011年 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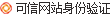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