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显著特征标志着中国科学30年的发展主线:逐渐从模仿和跟踪向自主创新过渡。而30年的实践也表明,基础研究的地基作用与我国科技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息息相关。
从更为人本的视角看来,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年轻一代研究人员正在更多地将科研视为一个平凡的职业,而研究的着眼点也更多地从兴趣和好奇转为结合国家和社会需求以及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这使基础研究的影子变得几乎无处不在。
随着科学界、中央政府乃至全社会对基础研究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基础研究也逐渐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在跟踪和创新之间
今年4月,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张先恩谈及30年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现状时说,总体而言,近30年我国科学研究活动大部分时间是在跟踪和追赶,目前进入比较活跃的创新阶段。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基础研究领域主要还是跟踪。”院士、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鸿烈说,“个别学科或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开始应用基础科学知识,解决中国的某个实际问题。因为国情不一样,能解决些自己的具体问题也代表着创造性。阐明某一新规律,创建一个新的理论,都是基础研究做的事情,这方面我们还没有重大突破,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重大创新的话,或许就会获诺贝尔奖。”
今年11月1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科研实力逐步增强,高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整体差距明显缩小,局部已形成优势;60%以上的技术从无到有,如今已进入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另有25%仍然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但在原来基础上有很大进步。近年来,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2007年全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出为174.5亿元,是1995年的9.7倍;用于基础研究的人力投入达13.8万人年,是1991年的2.3倍。
“但总的来说,30年来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发展还只是量变,并没有发生‘质变’。”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说,“如果要给我国基础研究领域,从跟踪研究到自主创新之间划条界限的话,我认为目前还划不出来。30年来,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积累还不够,我们还没有取得真正的创新成果,尤其是原创性成果。”
让创新的步子更稳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经济高速增长伴随而来的问题也逐渐凸显,怎样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许多瓶颈问题急需从深层次上探求内在的科学规律,急需从科技的角度提出破解的思路与方法。
“1998年,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启动。当时很有意思,有的部委提意见,说这是在弄概念,圈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姚建年说,“但过了两年,情况变了,我们国家对创新的认识空前提高,整个国家都在提倡创新型国家建设了,提倡自主创新。从居民、研究人员到中央领导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和重视有很大改变。”
1997年,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提出,“对于自由探索的研究工作主要依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面向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科学研究主要通过规划、计划的实施去推动”。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原国家科委组织制定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以此为标志,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的“973”计划正式启动。
2006年2月9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正式向社会发布。《纲要》指出,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已前移到基础研究,中国作为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更要强调基础研究服务于国家目标,通过基础研究解决未来发展中的关键、瓶颈问题。
今年初,科技部部长万钢在CCTV2007年度中国科技奖励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说,没有分子生物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研究,就不会产生转基因技术和相关产业。同时,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对基因的基础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转基因安全理论等又对相关的基础研究不断提出了新的课题,从而促进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不断向纵深发展。因此,“基础研究对我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论对科技发展本身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研究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制高点,必须进行超前部署”。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政策局局长韩宇在研究了美国、日本和韩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投入比例后发现,三者的共同特点是在其培育创新能力阶段,都加大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例如,日本在1967至1973年经济起飞初期,基础研究投入占R&D总经费的比例平均高达25%,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基础研究投入占R&D总经费的比例也高达22.9%。
韩宇说:“尽管不能把所有的创新都归结到基础研究,但是没有很好的基础研究,一切创新都是空话,最终只能是模仿,只能是引进。创新型国家今天在高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功,大多可以溯及其对基础研究的昨天甚至前天作出的战略部署;而今天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和支持,则为未来占领高技术发展制高点奠定基础。”
从兴趣到与国家需求相结合
如果将1998年启动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看作我国基础研究加速培育创新能力的开端,那么,2003年突发的SARS则可视为促使科学界将关注的目光更多投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的契机。
2003年4月23日,北京市政府发布通告,对非典型传染性肺炎疫情重点区域采取隔离控制措施。5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紧急启动24项有关SARS的基础研究。内容涉及易感人群研究、传染源与传播途径、病理学改变研究等6个方面。不久,31个“973”“SARS防治基础研究”课题立项。包括中科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在内的近50个团队参加了研究。
2003年底,中科院原副院长陈宜瑜院士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履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次年3月,在基金委全委会上,陈宜瑜明确提出了基础研究所关注的科学问题包括科学自身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来源”,其发展受“双力驱动”。
此后,陈宜瑜进一步阐述,牛顿、达芬奇、哥白尼那贵族式的研究方式早已经过去,基础研究的目的,已逐步从单纯满足科学家深化对自然现象和规律认识的兴趣,转向更加注重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国力竞争的需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基础研究的推动力已经大大超过单纯的科学自身发展的吸引力。
今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成都举行的“创新为民科技救灾”座谈会上说,从长远出发,中科院的基础研究、可持续发展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将进一步加强前瞻部署和综合交叉,积极探索和认知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孕育、发生、发展、演变及时空分布等规律和致灾机理,为科学预测和预防自然灾害和社会突发事件提供新的科学思想和理论依据,为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人类的幸福安康作出更大贡献。
“我刚回国时,包括我所了解的一些‘海归’学子,多数都是从延续自己在国外所做的研究开始,然后凭自己的兴趣寻找新的研究方向和课题。现在更多的研究人员是在自己研究兴趣的基础上,结合重大国家战略需求来寻找课题。而且,这种结合越来越紧密,因为研究经费是国家给的,同时国家的需求也非常明确。”姚建年说。
质变即将发生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近年来,不管2006年重庆特大干旱、2008年初南方特大冰雪灾害,还是今年5月发生的汶川地震,所有这些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和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科学界,包括基础研究领域反应之快是前所未有的。
5月15日,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基金委即启动“地震灾害的心理分析及援助”应急项目,并派两名研究人员赶赴地震灾区进行心理援助。此后,基金委地球科学学部、管理科学部相继启动研究项目,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目前公布的统计结果,2007年中国EI论文总数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中国科技论文总量保持世界第二。姚建年说,从中国化学会的情况来说,国际化学会这几年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今年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学术年会上,美国、英国、德、日化学会都是主席或主要负责人亲自带队参加。这几年我们的论文引用率也提升很快,这都说明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同行认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一个窗口,但从今年基金委化学部项目评审来看,专家认为有创新性的项目只占3%。这个比例太低了。”对于当前我国基础研究领域存在的不足,姚建年并不讳言。
“当然,也要历史地看中国的发展。”姚建年说,“尽管30年来基础研究发展很快,但积累还是不够。另外,我国的大产业不够发达,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也很少,先进产业的需求会催生很多新问题,会推动学科向前发展。”
姚建年表示,“我们目前原创性的工作较少,但我觉得这种情况很快会得到改变。一是我们全国上下对基础研究都很重视;二是投入也在不断增加;三是我们培养博士的数量世界数一数二,后备人才充足;四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基础研究已有了一些积累,量变有了,我相信很快就会发生质的提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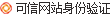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