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具有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的特征或精神气质。尽管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在某些科学家身上,不乏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例子,但是总的来说,科学毕竟是国际主义的或世界主义的。这一特征可以说得到学界和社会的公认。萨顿言之凿凿:“科学是仅有的一个对于全人类都是完全共同的事业……它是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奉行各种纲领的最有智慧、最广博的头脑联结起来的黏合剂。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从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发展中得到利益。”“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是国际的,是不同种族的人共有的,因此它是使世界各民族人民之间联合起来的最强有力的结合物。”怀特海注意到:“近代科学诞生于欧洲,但是却以整个世界为家。”作为科学家的萨拉姆深有体会:“科学现在是,而且一直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她现在是,而且一直是人类国际主义的最高体现。”J·金甚至断定:“科学是国际的。这不仅仅就概念上和精神上来说是这样,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永远也是这样。”
科学为什么具有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的特征呢?这是由科学的技术规范和科学方法决定的。它们保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似真性、普适性、一致性,是能够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或迟或早乐于接受和利用的,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诚如“科学家宪章”所载:“科学是进行观察,并对观察的结果作正确的推理,从而发现真理。无论是谁,都容易陷入谬误,或是眼界狭窄。为了逐步消除所有的偏见,就只有对各种观察结果以及从中引出的理论或预测这两个方面展开直率的讨论,才有希望获得真理。为此,全世界科学家的合作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科学的这种基本性质,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国际性的事业。”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决议这样写道:“自然科学是国际合作的一个多产领域。因为它本身就是国际性的,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基本定律是被普遍接受的。”玻尔深知:“科学在阐明我们的知识基础的努力中曾经团结全人类;科学是无国界的,它的成就是人类的公共财富。”中国学者任鸿隽也有真知灼见:“科学是有国际性的。这句话的意思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说科学是人类智慧的公共产品,科学知识应该公开出来为全人类谋幸福,不应由少数国家或个人据为独得之秘,阻碍人类的进步。另一方面,科学本身,须靠国际间学者的合作方能得到迅速的发展。若专靠一国学者的努力,不但会产生许多重复劳动,迟缓总是免不了的,有些工作的进展简直是不可能的。”他还表示:“用科学方法获得的真实知识,是有普遍性和一致性的,不因社会制度不同而有差别”,“无产阶级决无拒绝接受人类所积累的实践经验的意思”。
科学的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特征,更多地是由科学的规范结构即科学精神气质决定的,特别是科学的普遍性、公有性、非牟利性、自主性等价值表达,是支撑它的重要基石。卡梅伦言近旨远:“科学是本世纪人性最共同、最普遍的表达,是人性无国境的最完美的模型。科学家由于接受这些价值,可以作为理想的外交家出现。正如通俗科学作家阿西莫夫提出的:‘世界上的国家在文化、语言、宗教、趣味、哲学、传统上被分割开来,但是科学无论在哪里存在,都是相同的科学——科学家处处讲相同的语言,接受相同的思维模式,为在争取世界政府的斗争中寻找领导者,我们难道不应该面向作为一个社会等级的科学家吗?’”布朗言必有中:“现代科学不仅教导我们如何按照全球的尺度看待事物,而且也教导我们如何按照全球的尺度去行动,这在今日是极其宝贵的教训。科学追求独立于种族、肤色和信条的东西,科学事实上是在世界进行国际合作的最成功的范例;它比宗教和体育运动更成功,因为它相对地不受意识形态或竞赛的妨碍。科学的这一国际性特征通过国际科学协会联合会(JCSU)得到明证。”
说到科学合作,科学的本性,尤其是它的连续性、继承性以及它的广度之广、深度之深,也决定科学必定是一种合作的事业。合作可以是无形的、间接的合作:后人与前人、同代人之间在思想上的借鉴与启迪;也可以是有形的、直接的合作——科学中的一些领域和项目决非一人力所能及,甚至决非一国一蹴而就。因此,科学必须合作,科学是一种个人之间、国家之间的合作事业。萨顿对此了如指掌:“科学工作是国际合作的成果,这种合作组织日趋完善。”他还洞察到:“人们在科学创造中的国际合作是自发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和政治环境无关。”钱德拉塞卡也把科学的集体合作性视为科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因而科学家往往是国际主义者。也许正是看到科学合作的重大意义,雷斯蒂沃甚至把全球合作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科学共同体合作的示范作用上:“世界化根植于跨社会的或跨文化的运动,……‘国际科学共同体’被认为是这样的跨社会系统和超社会系统,科学家的活动被认为是世界化的关键性力量。科学家被定义为‘战略性的人力资本’和‘精英人物’,他们的规范取向是全球合作和世界共同体的发展的基础。”
我们强调科学的国际性或世界性,既不否认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也不否认科学家热爱祖国并为之服务。科学家虽然有自己的祖国,但是科学家毕竟是世界公民。很多近代科学家已经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爱因斯坦:他的祖国是德国,他最后的落脚地是美国,他本人是犹太种族,但是无论在本能、情感还是理智上,他都坚定地站在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谴责德国法西斯主义和美国麦卡锡主义,并且没有犹太复国主义的狭隘思想,从而赢得“世界公民”的美誉。莱曼(S. H. Lehman)称爱因斯坦“是伟大的世界公民,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巨人之一”。汤川秀树把爱因斯坦比喻为一头理想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大象。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尤西姆兄弟(John and Ruth Hill Useem)以至于把不同社会的科学家创造、共享和学习的文化式样称为第三种文化,并认为这一式样的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决定性力量,能够促进国际合作和全球统一。
许多思想家以至把未来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希望寄予科学的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与人类其他事务或文化相比,科学的竞争是和平的,科学的传播是和平的,科学确实也有利于和平。萨顿可以说是“科学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有利于和平”观点的热情鼓吹者。在他看来,“科学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的,这种程度在其他领域中是前所未闻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科学发现基本上同种族条件和国家条件无关,所以它们是团结与和平的主要工具”。不用说,对于科学的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特征及其正面功能,也有人表示怀疑或否定。但是,科学毕竟是天下之公器,这一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更何况,全球科学共同体的存在坚如磐石,其发展势如破竹,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势力根本无法抗拒和阻挡科学的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的潮流。否则,定会落个以卵击石、螳臂挡车的下场。
(作者系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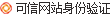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